访谈背景:2024年是广州大学法学院建院40周年,对广州大学法学学科而言,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和两位标志性人物:一是王珉灿先生离休后受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副书记叶选平(兼任广州大学校长)之邀,创办广州大学法学系,这是全国最早的以法学而非法律命名的法学院系;二是中国行政法学学科奠基人应松年教授协助广州大学于2010年成立广东省内首个公法研究专门机构,并亲自担任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两位敬爱的师长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和交集,特就两位师长为中国法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对广州大学做出的贡献以及两位师长之间交往的故事,采访了应老师。

应松年,1936年11月生,著名法学家,浙江宁波人。1960年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1961年被分配到新疆伊犁。1981年调西北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1982年在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从事行政法统编教材的撰写编辑工作。1983年起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担任行政法硕士生导师组副组长、组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制研究所所长。1995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担任法学教研部主任。2009年至今,受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一、法学先驱(/两位敬爱的师长之间的)的深厚渊源:王珉灿先生与应松年教授的交集故事
(一)应老师您好,请问您能回忆一下您与王老的第一次见面吗?
那是1982年,冬春之交,我到北京出差,听说司法部正在组织编写行政法的统编教材。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留意,是因为我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工作,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是想教授有些功底的法制史,但是行政法没有老师,学院让我把行政法接下来。我想那干就干吧,好在西北政法学院有全国最丰富的藏书,我就泡在图书馆里把当时能看到的所有行政法相关的图书资料都看完了。
我深感要开展行政法教学最欠缺的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教材。所以在听到司法部准备组织编写行政法教材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这件事恰逢其时,对行政法教学和科研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觉得我可以做一点贡献。我就直接来到了白石桥路44号,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对面,当时司法部法规司租用了其中的一层,作为国家统编法学教材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是一家装修非常简朴的招待所。我敲门之后,是时任司法部法规司副司长的王珉灿先生亲自过来开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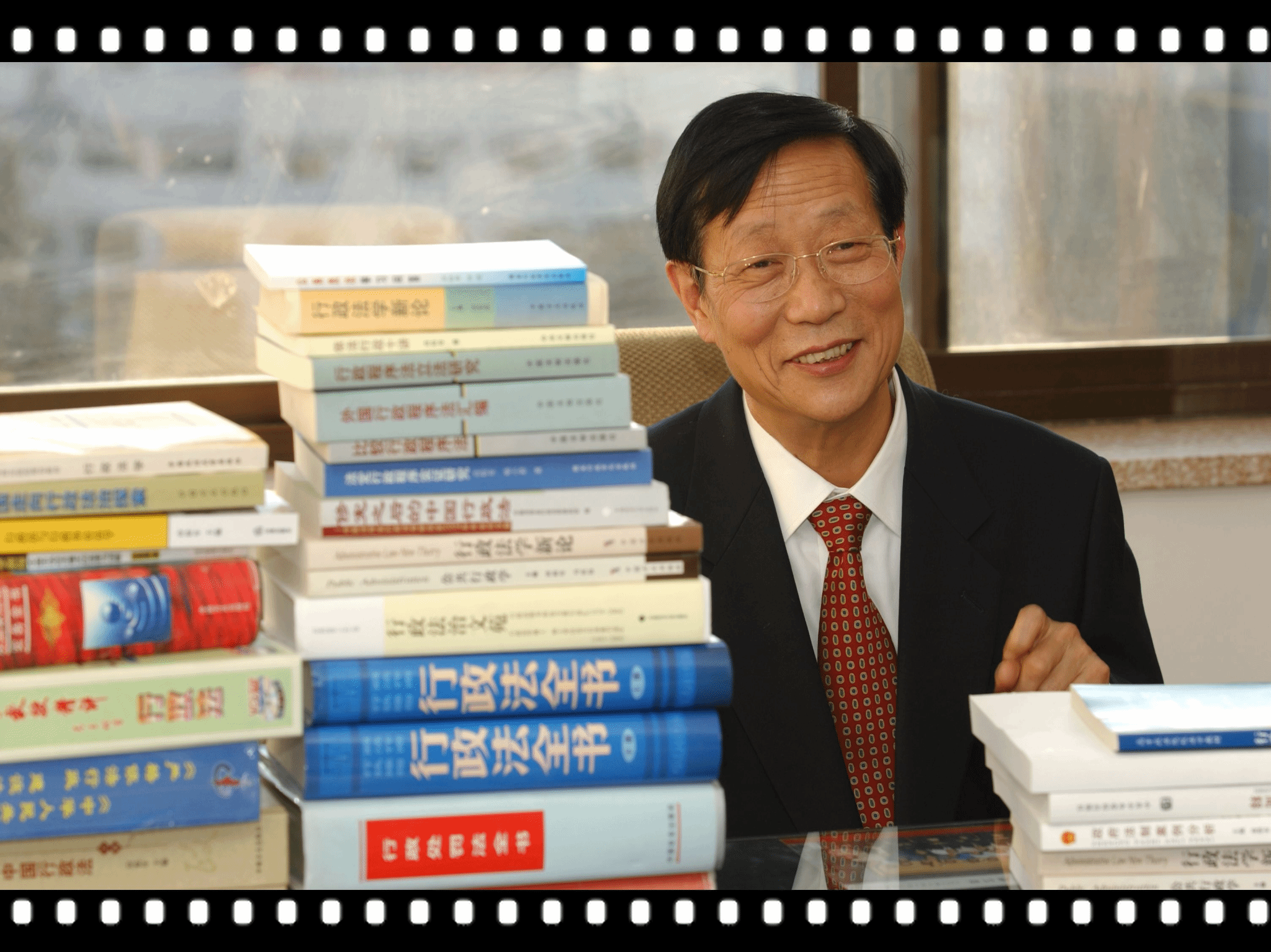
(二)您是怎样说服王老让您参加教材编写组的呢?
见面后我毛遂自荐:“听说要编教材,我能不能参与?”王老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你来吧!”他告诉我不久后要开会讨论这个项目,让我把地址留下。我回去后不久,法学教材编辑部的通知就来了,让我到厦门开会。1982年,在厦门参与讨论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契机。与其说是我说服王老让我加入教材组,不如说是我的肯学肯干的劲儿、我的学习热情和提前做的准备功课打动了王老。在来北京之前,我已经把西北政法学院馆藏的国内外行政法旧作都读完了,包括民国学者白鹏飞、范扬,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苏联学者司徒节尼金等人的著作,我还读了一些行政管理学书目,恶补行政法知识。那时西北政法学院的领导鼓励老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开阔眼界,我从西安出发,经过重庆、武汉,再到北京,沿途依次向西南、中南和北京的学者取经。对国内主要法学院校和老师关于行政法教学和教材编纂的想法和思路了解的比较清楚。在厦门的会议上,我就我了解的民国、日本、苏联的行政法体系以及行政法在我国的发展发表了意见,引起了与会众人的关注,也得到了王老的欣赏和器重。会议的第三天,王老问我在西政做什么?我说就搞行政法,没别的事情。他说你来法学教材编辑部吧,帮我把这本教材编出来。我太高兴了。王老做事情雷厉风行,他马上给我们学院写了一封信,把我借调到了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在他那儿编书。

(三)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件您与王老交往的事情吗?
在法学教材编辑部,我除了撰写分配给我的部分外,还协助王珉灿先生统稿。统编教材出来后,我又和朱维究老师编了一本资料选,里面附有行政法书目。王珉灿先生对我这一点很欣赏,说:你走到哪儿就把书目带到那儿,这是带研究生所必要的。我做学问和带学生,都延续了这个做法。做学问首先得看相关著作,古今中外都要了解;什么地方有什么书也要心中有数。下笔写某个问题时,必须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说明白,做学问不能“飘”。我在后来还陆续主编出版过好几本资料汇编的东西,就是想给将来学习行政法的人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阅读指引和参考。
二、公法研究领路人:应松年教授对广州大学法学学科的卓越贡献
1、应老师,请问您为什么愿意协助广州大学建立公法研究中心,并为广州大学法学学科的发展做出持续贡献?
广州大学法学系成立之初,师资力量不足,王珉灿先生从全国各地请人,那个时候的广州大学星光熠熠,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法律人才,为广东省、广州市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一代人,做学问、培养人才,一直都在不停思考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广州大学的法学学科是王老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能够接续他继续为广州大学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也是一种传承。
2010年前后,时任广州大学副校长的董皞教授,也是我的学生,想全面提升广州大学法学学科的国内外影响力,同时在行政法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希望通过独立的公法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立法、执法、司法和理论建设提供交流合作平台。我始终坚信,在法学分支学科中,行政法学是一门晚起的学科,却证明是最有活力的学科,并正在成为法学中的一门“显学”,我认为成立公法研究中心是非常有远见和必要性的。在担任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对于学生培养、学科建设与发展、科研能力提升、学术影响力提升等,我也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我来说,在党和国家推崇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鼎盛时期,我能够为法学学科发展、法治人才培养和法治政府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是我的幸事。所以我经常思考,我做的还不够多。因为身体和年龄的关系,这几年不能再到广州去,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2、想问问应老师您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
教师是一个好职业,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能把自己的理念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当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它能对实际产生影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3、应老师,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
当今中国整个社会已经走上了法治这条路,退不回去的。法治这条道路绝对不能变。法治在,社会就能够稳定。


三、寄语未来:应松年教授对年轻学子的期望
应老师您好,您能对学生们提几个学习法学的建议吗?
1、世间事,变幻莫测,实在难以逆料,所以每个人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品格。
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新疆,在那里种菜。我在劳动中很努力,营长说“这个大学生不错!”后来让我开展文艺活动,有时候需要去团部取电影,我在那个时候学会了骑马。有一次取了影片回莫霍尔,马受惊将我和影片盒甩在地上自己跑了,我在深夜一个人步行走在新疆的原野上,当时感觉惊险又凄凉,但事后回想只觉好笑。就像普希金说的: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我在新疆20个年头,赶上过饥荒,也因为右派被关过囚室,也曾经历过子弹贴着耳朵飞过,劫后余生。20年里困苦不少,温馨也多多。那些不同寻常的困苦,让我遇到了无数好心人,他们托举着我、救援着我、提携着我,使我深感人性之可贵、人情之温暖、人世之美好。青年人的人生刚刚展开,未来的路上风雨交加或风和日丽都是常态,要有毅力、有韧劲儿,始终保持乐观。无论在哪个环境里,都要踏踏实实把手边的事情做好。但我这个人始终都有一个特点:只要我接了一个任务,就认真干。种菜我就好好种菜,需要骑马我就学好骑术,要在农村扎根,我就做好农民,我自己盖起来了三间房和一个小院子,还在院子里种马铃薯。需要我搞好行政法,我也能把行政法搞好。
2、青年人学习要刻苦,准备要充分。
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两个学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董皞,一个是何海波。每次上课他们早早就到了,课堂上比谁都认真,每次讨论的时候都能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是很有分量的意见,能看出来是认真思考和准备过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他们两个现在都是著作等身的行政法学家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很开心。年轻学子有认真的态度、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3、要始终站在鸡蛋的这一边。
青年学生要关心社会、关心群众,这是学法学的人的基本担当。学行政法的人要永远站在人民这一边,要为人民说话。学行政法的人都不给老百姓说话,那老百姓怎么办。我曾经给我的学生们举例:“老百姓是鸡蛋,政府是石头。”如果让鸡蛋自己去碰石头,鸡蛋肯定碰不赢石头,所以我们就要站在鸡蛋这一边,要保护鸡蛋,不要被石头给打破了。老百姓与政府,一边是有权的,一边是没权的,那我们就应该站在没有权的老百姓这边说话。行政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促进人民的福利,没有这一点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学法律的人,知识学的再好,能力再强,忘记了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路就走偏了。我希望你们永远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不要忘记自己学习的目的。
4、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永不止步。
在我的青年时期,西北政法学院鼓励我们走出去看看,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要坚持研究些对实践有用的真问题,做学问不是几个人在书斋里玩,更不能把法学搞成玄学。要有开阔的眼界,重视交流合作中的学习,边干边学,始终跟着时代前进,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要考虑为这个社会、为中国的法治做贡献。
应松年教授专访视频
